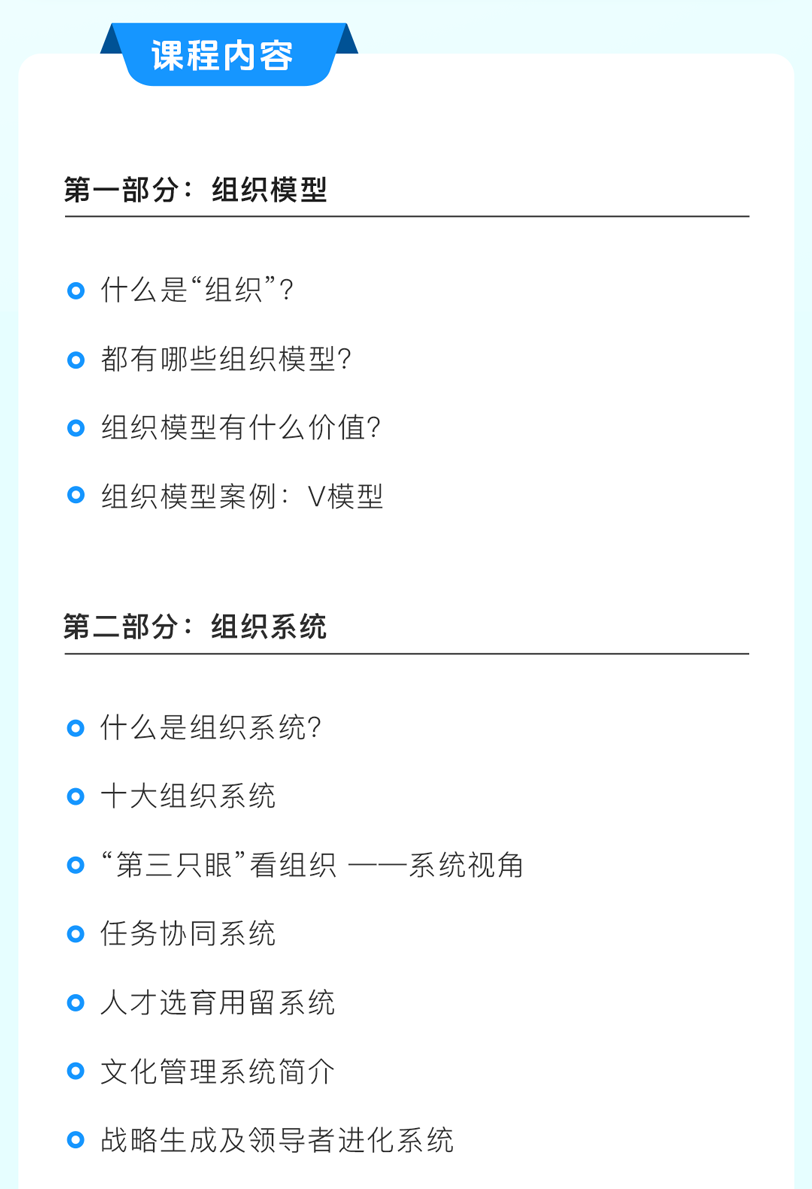房晟陶:处理复杂组织问题,要“先熵减,再解题”
正文字数:5100字
最近这两年,我接触过几位公司高层领导者,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些组织问题时,他们的工作思路一度“整得我有点不会了”。
这么描述吧:他们特别强调“解题”,习惯于说“这个问题怎么解?”
比如,“跨部门协同不太好,这个问题怎么解?”
这种工作思路,逻辑上很闭环、很精干。
更要命的是,道德上也很站得住脚:
“作为领导,不去解决问题,那要领导干什么?”
“领导提出要求,我们得尽快有措施落地啊。”
“你不是专家吗?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解决不了?”
对于这种工作思路,你还真是难以反驳。如果反驳,自己都觉得有点“佞臣+白左”的嫌疑。
但是,我对这种工作思路,有浑身说不出的不适感。我的身体感受,加上我多年组织工作经验告诉我,这种“解题思路”对于处理“复杂组织问题”是不适合的。
不过,如果你想反驳他们,你不能只说“你这个思路是不适合的”。
那相当于“以玄学对抗逻辑学”,毫无胜算。
“为什么不适合?”
“这种思路不适合,那什么思路是适合的?”
“你给我演示一下什么是适合的?别光说不练啊。”
…
后面一系列的反问你都可以想象得出来。
我们得用说得明白的系统逻辑学来对线性逻辑学。
在过去这一两年里,我和这种不适感时不时地对话,在实践中不断观察总结,积累论据,梳理论述方法。
直到最近,我才可以比较肯定和舒适地做出论断和建议了。
简单来说,我的论断和建议是:对于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不能用“解题思路”来处理,而是要“先熵减,再解题”。

01
COOSTRATEGY
什么是“棘手问题”?
我借用了“棘手问题”这个概念来阐述我的观点。
“棘手问题”,英文是“wicked problem”,是1973年由公共政策学者霍斯特·里特尔(Horst Rittel)和梅尔文·韦伯(Melvin Webber)提出的概念,指那些极度复杂、边界模糊、难以定义且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社会或系统性问题。中文有的时候也翻译成“邪恶问题”、“抗解难题”。棘手问题无法通过线性逻辑或单一学科知识解决,其挑战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冲突和动态变化的环境。
棘手问题的核心特点有以下这些:
无法明确定义:问题的本质和范围难以清晰界定。例如,“如何减少贫困?”可能涉及经济、教育、政策等多维度因素,不同视角对问题的定义可能截然不同。
没有终极答案:不存在“正确”或“错误”的解决方案,只有“更好”或“更差”的尝试。例如,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需要长期验证,且可能引发新的问题。
解决方案不可逆:每个尝试解决的行动都会改变问题的背景,甚至导致新问题。例如,某地区通过修建大坝解决缺水问题,却可能破坏生态平衡。
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:每个棘手问题都是独特的,无法通过既有经验或模板直接套用。例如,新冠疫情与历史上其他流行病在传播方式、社会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。
多方利益冲突: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冲突。例如,城市旧改更新项目可能面临居民、开发商、政府之间的诉求矛盾。
深层系统性原因:问题根植于复杂的系统结构中,单一干预难以奏效。例如,教育不公平可能关联经济差距、文化观念、资源分配等多重因素。
无明确“终点”:无法通过达成某个目标宣告问题彻底解决,需持续调整。例如,社会公平问题会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。
以这样的标准来看,在国家和社会层面,肯定是有很多“棘手问题”的,比如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危机,等。
与“棘手问题”相对照的叫作“良性问题”(Tame Problem),指的是那些边界相对清晰、目标相对明确、解决路径可预测且存在已知解决方案的问题。

02
COOSTRATEGY
组织问题是“棘手问题”吗?
一个公司的组织问题,比如“跨部门协同不太好”,算的上是“棘手问题”吗?
我的观察是,很多中大规模的公司,都已经创造出了一些“棘手组织问题”。
如何判断一个组织问题是否属于“棘手问题”?可以对照“棘手问题”的一些特点来衡量。
是否难以明确定义?如果问题边界模糊(例如“跨部门协作效率低”可能涉及沟通流程、激励机制、文化冲突等不同层面),且不同角色对问题的认知差异显著(例如管理层归咎于执行力,员工抱怨资源不足),则属于棘手问题。
是否存在深层系统性关联?例如某公司“创新力不足”可能涉及:组织结构僵化(层级过多抑制创意);绩效考核导向短期结果;跨部门资源争夺导致合作困难;领导风格压制风险承担。这种多因素交织、需系统性调整的问题符合棘手问题的特征。
解决方案是否引发新矛盾?例如为提升效率强行扁平化管理,可能导致决策混乱;为加强控制推行严格KPI,可能扼杀员工主动性。这种“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更多问题”的循环是棘手问题的典型表现。
是否涉及价值观冲突?例如家族企业中“元老派”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博弈,或科技公司“增长至上”与“员工幸福”之间的取舍,这些涉及根本价值观对立的冲突难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。
以这样的标准来看,典型属于“棘手问题”的组织挑战是:
组织文化转型:例如从“层级制”转向“敏捷组织”,需改变员工行为习惯、激励机制和权力结构,过程中可能遭遇隐性抵制和文化反弹。
跨部门协同低效:部门目标冲突(例如销售部追求客户数量 vs. 服务部强调服务质量)、资源分配不均、信息孤岛等问题,需重新设计流程并平衡多方利益。
战略与执行脱节:战略方向清晰但落地困难,可能源于中层管理者认知偏差、基层能力不足或激励机制错配,需多层面干预。
代际或文化冲突:年轻员工与资深员工对工作方式、沟通风格的矛盾,或全球化团队中的文化差异,需协调不同群体的价值观。
当然,并非所有组织问题都属于“棘手问题”,很多组织问题都属于“良性问题”(Tame Problem)的范畴。例如:
报销流程冗长:可通过数字化工具和规则简化解决。
操作技能不足:可以通过课堂培训、实践辅导等标准化方案提升技能。
项目人手不足:可以通过招聘或外包快速缓解。
这样的组织问题,有点逻辑思考、根因分析的“解题思路”就可以了。
当然,也会有一些问题,介于“棘手问题”和“良性问题”之间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复杂组织问题”。这样的问题,就得有多维度思考或系统思考的能力,“故障排除式的解题思路”就已经效力不够了。
比如猎头不给力:是对合作猎头顾问沟通赋能不够,还是猎头公司选择不对,还是公司的人才画像不合理,还是公司的声誉不太好。
“复杂组织问题”中的一部分,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应对,就会演化为“棘手组织问题”。
例如,“跨部门协作效率低”,就成为了有些公司的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“创新力不足”就变成另外一些公司的“死穴”。
对于这样的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作思路来应对?
我的建议是,应对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要将“解题思路”迭代进化为“熵减+解题思路”。换句话说,要“先熵减,再解题”。

03
COOSTRATEGY
“熵减思路”vs“解题思路”
请先让我把“熵减思路”和“以根因分析为代表的解题思路”来做个对比。
很多人认为“熵减”就是“更深入的根因分析”。比如,有些人理解的熵减是:你要消灭苍蝇,不能只在灭蝇的工具上创新,还得解决一下产生苍蝇的粪坑。这是一种误解。
这个思路还是属于根因分析的解题思路,还不是什么熵减思路。
这两个思路的目标和方法论很不一样。
熵减思路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减少系统的混乱度(熵),使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变。关注的是整体系统的优化,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(当然不排除阶段性解决某个问题)。熵减思路关注长期、持续的过程,强调动态平衡和持续改进。
以根因分析为代表的解题思路的目标是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,从而彻底解决问题。关注的是具体问题的深层次原因,强调逻辑推理和因果链的追溯,而不是系统的整体状态。以根因分析为核心的解题思路更关注短期、一次性的问题解决,强调快速找到原因并采取行动。
用英文来说,“解题思路”就像是“troubleshooting”;类似于汽车修理中的“故障排除”。

04
COOSTRATEGY
“解题思路”有什么局限性?
用“解题思路”去应对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会有很大局限性。
第一个局限性是“为错误的问题找答案”。
领导们一上来就问“怎么解”,好像所有问题都像修车一样,都可以找到逻辑的答案。但是,很多时候,问题本身就是错的,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的核心。结果呢?下属以使命必达的心态,拼命为错误的问题找正确答案。
“为错误的问题找答案”的替代是什么?重新界定问题。
第二个局限性是“总是从问题出发,缺乏以终为始的牵引”。
“解题思路”总是盯着眼前的麻烦(所以,troubleshooting这个词还是挺形象的),缓解眼前的痛苦,但却忽视了公司在应该打造什么特色能力(是快,还是技术创新,还是精细运营)。一个动物,如果总跟大象去比体重、跟猎豹去比加速度、跟鳄鱼去比两栖能力,那么,必将满眼都是问题。关键是,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?
“从问题出发”的替代是什么?以建立战略性组织能力为牵引来筛选哪些问题优先解决,哪些问题不是问题,哪些问题必须忍耐。
关于战略性组织能力这个概念,请参见《什么是组织能力?什么是战略性组织能力?》这篇文章。
第三个局限性是“追求短期变化,来回拉抽屉”。
秉持“解题思路”的领导们,特别想要看到短期的成果,希望三个月内就看到“可感知的变化”,“砸钱也至少得听个声响”,要给自己的努力一个交代,也给领导的殷切期望一个快速的回馈。结果,虽然短期内确实有“挪动”,但一年后又恢复原状。
“来回拉抽屉”的替代是什么?治大国如烹小鲜。或者说,拐大弯,拧螺丝。
以上这三项就是“解题思路”在应对“棘手组织问题”时的局限性,当然不仅限于以上三项。
在你的组织里,有没有这样的现象?

05
COOSTRATEGY
“熵减思路”有什么不同?
熵减思路下,领导者的动作也会有显著不同。对于“棘手组织问题”,他们会首先在以下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。
这三个创造,是解题思路吗?这几个动作,都是作用在组织问题产生及解决的机制和土壤上,而不只是在问题本身。
这三个创造,对做好组织工作重要吗?真正处理过复杂组织问题的人都明白。
熵减思路的领导者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用力点?这是因为他们深知,解决棘手组织问题就是在挪动一大群人的认知、偏好、利益、能力、价值观;组织问题的相关方们在这些方面的模糊、冲突、表里不一、统一但缺乏竞争力等等,这就是熵增的核心原因。
相比之下,“解题思路”下的领导者,动作更多是聚焦在PDCA,项目管理,或者OGSM。他们会规划策略、制定计划、明确责任人、推动执行、检查结果、奖励及惩罚、调整行动。这种思路在解决“良性问题”时很有效,但在面对“棘手组织问题”时,往往是没抓住重点,或者明知这么做不对,但不愿意去触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令人烦心的事项。
于是,在这种“解题思路”之下,很多公司的组织问题“越解决越多”。

06
COOSTRATEGY
从“解题”到“熵减+解题”
但是,这并不是说“解题思路”是错的。
愿意去“解题”的工作热情还是要认可的,但不能过度使用。“解题思路”或者说“troubleshooting”思路的过度使用,业务出身的高层领导者经常发生。甚至,那些越擅长“解决问题”高层领导者,就越要注意将“解题思路”进化到“先熵减,再解题”。
更重要的是,“解题思路”要被用在合适的问题层次上。
对于公司的一、二级组织问题(比如公司整体组织设计问题、核心职能如营销的组织定位问题、一级组织系统如人才选育用留系统的设计问题,等),必须首先、主要使用熵减思路。
但是到了公司的三、四级组织问题(比如营销职能之下的部门/团队设计,人才选育用留系统的模块设计,等),因为其复杂性降低,以解题思路为主是可能的。不过,对这类问题使用解题思路的前提仍然是其上一级组织问题的熵减(比如营销职能的整体设计和熵减、人才选育用留系统的整体设计和熵减)。
谨以此文与正在与组织问题搏斗的高层领导者们共勉,希望对他们能有所启发,用更多“先熵减,再解题”的思路来处理组织问题。
更重要的是,希望这种思路能够帮助他们在规模中小的时候,就避免很多“复杂组织问题”演化为“棘手组织问题”。
首席组织官
▼ 关注我们,共创美好